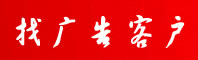- ·广告人的高傲与浅薄 是时候跳出
- ·原来广告人有那么多超能力
- ·致广告新人:广告是一场幻觉,不
- ·广告人不能承受的『委屈』和『误
- ·广告人接私活时到底怎么开价?
- ·大学生如何成为一名广告人
- ·广告人各职位撒谎能力大曝光
- ·十年广告人怎么写高考作文
- ·谢霆锋当创意总监为广告人提气
- ·本网站【微信公众号:中国广告人
- ·中国广告人网站官方QQ群欢迎加
- ·一位前广告人的心声:你们非得把
- ·“广告狗看进来”你是哪条狗?
- ·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死的广告人
- ·别自恋了广告人,庄淑芬是谢幕不
- ·广告人眼中的4A是怎样的?
- ·一个传统广告人的自白
- ·老广告人的反思:定位理论是大忽
- ·定位理论是大忽悠?—一个老广告
- ·广告人的时代来了
- ·一个老广告人的30年故事
- ·看,广告人如何写高考作文
- ·传统广告人该何去何从?
- ·正在“消失”的广告人
- ·一个广告人的独白-社交媒体的痛
- ·光棍节谈广告人的单身与梦想
- ·广告人,你是一个思维的懒虫吗
- ·广告公司能实现广告人的抱负吗?
- ·以广告人的思维看道德
- ·广告人应该对阳光下的一切都感兴
- ·广告人原则
- ·一个广告人的营销观
- ·80后的广告人为何暮气沉沉?
- ·广告人网站手机客户端(安卓版)
- ·从汤唯绯闻男友走红看苦逼的广告
还记得在九五年八月九号,我晚上刚飞抵上海的办公室,助手告诉我,台湾达一广告的Richard Huang传来一个口讯:徐一鸣在昨天被送进了台大医院,证实得了血癌,病况危殆,恐怕他已无法再为龙吟榜写文章了。
当时我心头打了个冷颤,数天前还跟PETER(徐的洋名)在电话里投诉,为何台湾广告界,对龙吟榜的反应这么冷淡,虽然催促连连,但送来的作品,无论质和量,都跟台湾这个市场的广告不成正比。PETER当时还笑说,我这个香港人,根本不了解台湾广告人,让他写篇文章,在台湾骂骂我这个天真的香港广告人
笠日,我请助手致电台北,查问徐兄的病情,得到的回复是:「大家都已做好了心理准备。」
我是去年(1995)父亲节当了血癌爸爸,住进台大医院的。
其实,早在六月中我公司赴美加旅游时已有徵兆,只是我当时不以为意总以为案牍劳形倦乏了,想抽空多游泳跑步就行,谁知回国后越游越黑、越跑越糟!病发当晚给救护车呼啸送到台大时,血已经比正常人少了近3000cc,全身皮下渗血不止,血压低到30、60,心知不妙。第二天早上医生面告我得了血癌,没吓到我这饱受沧桑的广告人(我当时只想这下玩完了),倒吓坏了在旁的悍妻与闻风而至的两位客户大人,(怡富投资顾问公司的章嘉玉和李挺生)病的学名是「急性前骨髓细胞性白血病」,俗称M3型血癌。有趣的是,对我开广告公司的第一个客户瑞泰人寿来说,我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他们理陪的客户,嘿!嘿!金额可是我做广告以来最大的一笔外快。
九月的一个周末,我应中国时报之邀请,到台北当世界华文广告奖的评审,事前与达一广告创意部的Richard相约好,晚上带我到医院,探望这位认识了五年多的朋友。
在时报招待各评审的晚宴上,大家才吃了一半,我便中途离席,也未顾及会否得罪主人家。在门外赫然看见跟我会合的Richard,跨下有部小摩托车,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,我从来没胆量坐<人体包铁>的摩托车,只有硬着头皮骑上车背的后座位。
台北的街头,对外来人来说,到处都是如狼似虎的大小汽车。小摩托车在互相交错的车头灯下穿插,左右倾斜扭动,我心里发毛,手心出汗,但总不能从后面拥抱Richard 来给自己多点安全感,(这样做,既有失香港创意高手的威望,更有可能令Richard误会,我是那种喜欢狎弄年轻小伙子的老色魔。)我只好双手死命抓紧座位后的把手;那短短十数分钟的车程,对我来说,是毕生难忘的经历。
到了台大医院,我又是另外的一副心情,刚踏出电梯,便看见走廊日光室的长椅上,除了坐着徐一鸣和徐嫂嫂外,还有他的三数位学生。Peter看见我,费力地站起来与我握手,他个子比我高,但此刻看来却像个衣架子,与及一双消瘦的腿。
那时侯,他连跟我说话,也好象刘易士刚跑过一百米般喘着气。
Peter说七月中作全身检查时,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,所以被送进医院后,当医生告知他是得了血癌,可能只多活一星期时,他愣了一下后,也只好认命了。
接受了这突然而来的现实后,基于创意人多年临危而不乱的培训,Peter开始替自己,家人,和广告公司作出安排。我强忍着心酸,觉得说一般安慰的话,是没什么意思,只有默默地听Peter继续谈他的抗癌经历:跟着的日子,Peter是靠不断输血和坚强斗志来给自己多抓一点时间的,他笑说:就这样,已快成为台湾血癌病患者生命赛跑的记录保持者了。现在病情已稳定下来,医生说他应该可以多活三个月。跟着便要看看化疗的成效。
我从来就是个感情用事的人,在这次会面,一直没有多说话,而且尽量掩饰沉重的心情,反而Peter还是保持他一贯的幽默,说在医院里,现已成为了大哥大,医生让他「想做就去做」;他知道我未用完晚饭,嚷着要陪我到外面吃豆浆油条,还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与我见面,要好好地泡泡。看着他和坚强的徐嫂嫂,我感到自己很渺小。
九四年,当我完成世界华文广告奖评审后,我对华文广告的前景,充满了希望,就在台北飞回香港的归途,决定创办龙吟榜。
但九五年,我当完评审,从台北飞回香港时,脑海里茫然一片;人生旅途,实在变幻莫测。
说真的,我在台大的治疗过程实在是不堪回首:第一次化疗的份量虽轻,滋味却重得难以消受,斯时才深深体会苏东坡老兄「一吐为快」的真正意义!做完七天化疗后,我的白血球迅速降到谷底(当时我的白血球只剩两百,正常人应该有四千至十万颗),全身毛发也毫不念旧地弃我而去,也就在这几天等待期里,趁项上青丝犹在,我参加了两个原本不可能出场的比稿,一个是汉来大饭店,一个是京华投信,他们现在都是达一的客户了。
第二次化疗份量是上回的三十倍,白血球从谷底到谷底的谷底(剩约一百颗),全身因过敏而红肿,苦则苦矣,头痛发烧居然无日无之,实在是难得的经验。幸亏有国手吕明进教授暗中(台大相当排斥中医)照顾而「轻」骑过关——可叹我成了病房当时最佳男主角——两周内,体重足足减去十五公斤,两寸半腰围不翼而飞,省下瘦身美容费少说一、二十万,咳咳,好爽好爽,咳咳。
俗话说「花无三日红」,第三次高剂量化疗后让我几乎驾鹤西天、魂归道山。
今年二月五日中午急送台大隔离病房时,体温摄氏42.3度,拼命灌下2000cc温开水,仍旧浑身「热情如火」,迷糊中挨了不少针,夜半悠悠醒来,再度捡回条烂命(广告人不死,只是欠修理?)。可这一住就住了个把月,有那么一阵子白血球尽在50颗上下徘徊,夸张些说,蚊子咬下去他妈的就翘辫子了。农历新年,全家就在台大12D禁声度过,每天坐看血液检查数字踏步上爬为最大乐趣,可喜悍妻成了弱妻,稚儿倒成了健儿,相对医院外为选总统而一片厮杀的光景,这里头吞药挨针输血抽骨髓的场面平静多了。
三月初出院,恢复上班、教书,又是好汉一条!逍遥没几天,又遵医嘱五月八日再入院,九日全身麻醉抽存1080cc骨髓,为一旦复发或化疗无效时先做好自体移植的准备(骨髓有效先决条件:一年以上血里没癌细胞跑出来),五月十日夹着蜂窝屁股出院,继续奋斗!
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,我与当时的未婚妻(今天的太太大人),利用圣诞节假期,到了台北探望Peter和徐嫂嫂。那时侯,他病程继续稳定下来,只需要定期回医院治疗。原本要到他家里探望他,但Peter还是那副好客德性,坚持要到君悦酒店接我们,说徐嫂嫂会开车送他来,但见面时,车却仍是由他驾驶。
那时侯的Peter,因为经过化疗,已掉光了毛发,脸孔有点臃肿,不过人却是很精神活泼,仍然保持一贯幽默感和台北人开车的心狠手辣,(尤其是佩服他窄路突围而出的技术)。从吃台菜,到带我们买普一的牛肉干,都不停以他的病情为题说着笑话。
我的另一半,平时很喜欢吃台菜,但此刻的她,并没有多下筷。事后,她对我说,看到徐嫂嫂的坚强,Peter的积极,自己只有强忍心里的难过,哪还有胃口吃东西。
Peter说,除了治疗之外,他现在常常花时间到医院,给刚刚获知得了血癌的病人,作业余的心理辅导。自己是过来人,绝对了解那种惊变心景,他希望帮助每一位难友,从消极转为积极,去对抗病魔。听到这里,我的另一半紧握着我的手,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,Peter跟徐嫂嫂实在令她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。
分手的时候,Peter还再旧调重提,问我俩何时结婚?还答应到时一定回到香港喝喜酒。(后来,他还是因为起行前才发现签证过了期,无法实现他的承诺。)
Jimmy(林俊明的洋名)到病房那天,我只有两百多颗白血球,照理说是不能会客的,但我实在不想老躺在床上,「有朋从香港来」便成了让太太放行的好借口!诗云「身经多难情越好,未觉人间古道沦」,的确,当我病痛最苦的时候,朋友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力量。像以前李奥贝纳老同事余湘三番两次亲自跑来看不说,一天到晚还送水果送书,实在让人感动不已。当然还有许多许多朋友来给我加油打气,我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这些朋友的名字(有些我根本不认识),但是我真的感激的不得了,所谓「一死一生,乃见交情」,坦白说,我这个病不知道能拖多久,眼见几位血癌病房里交的患难病友先我而去,更觉得人生无常,总希望把握机会全力做好想做该做的事,庶几乎让人家觉得自己来世上并非白走一趟。遗憾没参加Jimmy的喜宴,实在也是病呆了,订了机位却没想到自己的到港签证过了期。
经过化疗后,Peter的病有好转了,离开医院后,他开始每天上午上班,公司总是要照顾吧,我差不多每三数星期,都会在早上挂电话到台北跟Peter聊天,不过,渐渐发觉每每找不到他,因为他大多出外开会了。
就是找到他,还是要听他在电话兴奋地说,今天又拿了一个什么什么客户!大哥呀,为何你不花多点时间跟家人相聚,现在你的每一分钟都是这么宝贵,为什么还要这样拼命,是舍不得广告公司?还是必须把公司业务支持下去?再问一句:你会后悔做广告吗?
其实,除了吃健保不需给付昂贵的中药外,我在西医方面的治疗已经告一段落。只是每个月回医院门诊抽一次血,看看有没有癌细胞跑出来而已。前一阵子朋友介绍一位大陆异能师父,强调可以发功治病,我做广告这行做久了不太容易信这个,只有自求多福。
Jimmy问我为什么还在上班,我第一个想到的答案就是「不上班要干什么」。从我生了病开始,我就抱定「做最坏的打算,求最好的结果」。所以,我只要能动就不静,我只要能站就不躺,我只要能走就不坐,只要出院就去上班。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:我尽量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,我也许就不会是一个病人了。这,就是为什么我住院时还在工作、出院时还在上班的答案。
他说我「现在每一分钟都那么宝贵」,我倒想请问他:现在的每一分钟和以前的每一分钟有什么不同呢?我总觉得,一个人要到得了血癌之后才发觉每一分钟都是那么宝贵,那他真的够悲哀了,这好象是在说:人必须得了绝症后才会发觉时间是那么宝贵,才要好好珍惜,不是很奇怪吗?我不太知道别人得血癌怎么想,至少我不是这么去想,从小到大,从大到生病,时间对我一直都是宝贵的。你可以问,问任何和我相熟一点的朋友、同行或学生,生病前我是怎么样在过日子?我是怎么样在做广告?我是怎么样在教学生?其中比较明显的不同恐怕只有说我脾气改了一些(但也只是「一些」而已,脾气本来就随着年岁在改,生病最多只是逼我改快一点)、在家时间多了一些、以及银行里原本就少的钞票更少了一些!
说到这里,我一定要纠正Jimmy大佬你一个观念:血癌是不好玩,但却不是绝症。就算是绝症罢,我也不会后悔把精力花在广告上,难道说,死于糖尿病的蒋经国会后悔把精力花在做中华民国总统上吗?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在广告公司里,你一定听过「这样子铁定没救了」、「完了,这次我真的完了」、「天哪!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」之类的话,这和我在台大血癌病房经常听到的好象没什么不同,可见做广告又何尝不是另一种「绝症」?
患了病,对身体已是折磨,还要动脑做广告,对于患病后的创意思路,Peter有他一贯幽默的理论:生病后,创意思路更跨了一大步!?是耶非耶,由台北的广告人当评审员好了。
没错,生病后,创意思路确实算是又跨了一大步。原因是,一生病你脚步自然慢了,脚步一慢你时间也就多了,时间一多你想事情也就更从容不迫了。刚好,医院这种鬼地方你除了睡觉之外就只能想想事、看看书,偏偏看的(大家送的)全是些「不生病绝不会看」的书(如佛经啦!血液学啦!静思语等等),大半年下来,化疗过程仿佛就是图书浴,本来做创意就是跟自己打仗,我本来就身经百战,今番又以战养战,回到创意工作上当然有比以往更宽的路子(此处纯属私人看法,创意思路不佳者万勿以身试法),这阵子提案就十分顺利(也可能客户大人担心弄出人命,不敢不给面子)。总之,生大病逼我提前做了打烊收山的准备,就是现在死,也已经赚到了,更何况有如林俊明大佬等好友三番两次的关心照顾,我不加油怎么行呢?
多嘴问问Peter兄,你的客户和公司员工,在知道你患病危殆的时候,在精神和实质上,给了你什么支持?但是日子久了,这些支持,又是否有变?
说到这里,我一定要甘冒阿谀客户之嫌,借龙吟榜篇幅谢谢他们。当时,我的客户大概把我生病看成不景气的一部分,骂骂李登辉就算了,对达一倒是依旧支持;我部门当时因为缺乏较资深的员工,凝聚力显得就比较弱。不过,在达群兄领导下,台大医院仿佛成为我们的分公司,连线作业相当顺利,总算是强渡了几回关山,其中,把台北县刘盛良先生高票送进立法院算是我们在逆境中的代表作。你问的没错,对达一这种战斗型的小公司来讲,老板经常生病住院当然不太好,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度发生,所以,尽管我现在已经恢复上班,还是增聘了几位好手助阵,希望先把手上客户做得更好,未来才可能开发其他的新客户。
以前,每当我在台湾广告界面前,提及徐一鸣,他总是得到毁誉参半的评价,有说他可以算是台湾广告界的才子,但是持才傲物,树敌众多。对于我这个并不属于台湾广告圈的港巴子来说,并没有考究的必要。
我跟Peter的相识,是九零年我在香港灵狮当行政创作总监的日子,当时灵狮的亚洲网络,跟另外两个跨国广告公司网络,为一个泛亚洲区的法国洋酒客户在比稿,灵狮从各单位中,抽调创意精英到曼谷的亚太总部,集成主打部队,成员之中,只有我和比我高大魁梧的Peter是华人,其他都是不同国籍的亚洲人和洋人。抵达泰国后的晚上,我们被接待到主办单位的总经理府邸吃泰国菜,席间我与徐礼貌地互敬了X.O.洋酒。
隔天,我俩被编进同一分组内动脑,主导的亚太区创意总监告诉我,这个从台湾灵狮来的创意人很棒,但不懂英文,要我当他的翻译:但是,他们可不知道,那时侯,我这个香港广东人,讲国语一点也不成!(Peter到今天仍然觉得我的国语还是不成。)要用国语跟他沟通,我的舌头累,他的耳朵也不好受。经过数轮对应,我发觉Peter在装蒜,他的英文应该是可以的,想是他这人高傲,不原在洋人面前操英语吧。后来我索性对他讲英语,他跟我讲国语,余下的以书写补充,开始互相冲击彼此不同的创意。
慢慢地,我俩都觉得对方的创意还可以,就这样,我俩提交了数个满称心的创意,其中一个被主导的亚太区创意总监,选为可以进一步雕琢的创意之一,无独有偶,我俩在翌日都同被所属单位,紧急召回应付各自客户所引起的突发性地震。基于大家都有副傲骨子,我跟Peter自此一直保持联系。我到台北时,找他喝酒,他到香港时也找我喝酒。
想到与林俊明相识相知的经过就感慨良多!那次去曼谷有两大收获:第一次见识泰国浴和认识他。那晚由于泰航误点,我到机场时已是午夜,见到他后知道竟然有人会说(很烂的)天朝语言,安心不少,就打定第二天靠紧他不放的主意,果然一切OK,第二天晚上曼谷灵狮一位老兄带我「见识世面」,因为与林俊明不熟就没拉他去(现在碰到大嫂也比较心安理得),可见有时候好东西还是只能独享!
此后,我们偶有往来,直到93年夏天才算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,那瓶X.O.居功厥伟!我在他那豪宅整整聊了一晚,称得上是「酒酣说剑、耳热谈天」,那晚夜凉如水,月色甚美,加上醇酒助兴,说起话来铿锵有声,至今教人难忘,抚今追昔,不免时有「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」之欢。
我很怀念那一年的仲夏夜,在我家的小露台,Peter跟我,遥望挂在浅水湾头的明月,不断交换创意心得,还喝干了一瓶X.O.呢。
愿我们快一点,可以再次把酒论广告。